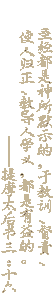兩約之間(續)
“兩約之間”的這一段時期,是從舊約的正典之末開始的。茲分三方面來論︰
一、歷史方面
為了重新複習歷史,最好我們是看一看舊約末后時代的波斯整個時期。此一時期是從波斯的初王古列算起,即主前538年,直到亞達薛西王死后為止,即主前424年。古列王不但記載在舊約中,歷代志下,以斯拉記,以賽亞書和但以理書都提到他,就是希臘人對他也是熟知的。他因于主前538年征服巴比倫而聞名四海,使他成為當時古代世界的唯一統治者。在猶太人的歷史中,古列是一個重要人物,因為他對猶太人采取寬大政策,所以容許他們回歸帕勒斯坦,重建久已毀壞的文明。由于古列的仁慈,聖殿的崇拜得以恢複,以前被尼布甲尼撒所擄去的聖器,于今都歸還給猶太人。
在被擄時期,猶太人的房屋田園均皆荒蕪,百廢待舉,首先他們的房屋得以重整,繼而聖殿得以再建。複員計劃開始于主前536年,于廿年后重建完成。但于此期間,從北方來的撒瑪利亞人以及鄰近諸族和過境的軍旅受到許多的阻擾。
肯白西(古列之子)則遠不如其父,他是一個愚昧、狂傲和殘忍的人。于主前522年死去,由大利烏繼位,他把波斯帝國分為廿個行省。猶太人在大利烏的治理下得享太平,但國勢日衰,民族氣氛逐漸消沉。所以當時需要哈該于撒迦利亞的預言信息重新振發他們的愛國熱忱。以斯拉記第六章第十六節描寫到百姓因建殿完成而歡欣,但想到從前所羅門所建聖殿之威容,和目前所重建的聖殿一比,相形之下他們慶祝的心情就不得不受到限製,大有今昔不同之感。于主后486年大利烏于人類歷史中最為決定性的戰爭中敗北身亡;那就是歷史中所記載的馬拉孫戰役,于此希臘將軍麥提底的大兵打敗了波斯的軍隊。
大利烏的長子亞哈隨魯于主前485年登極,廿年后被暗殺。他的兒子亞達薛西繼續他作王,他受到以斯拉的感化,準許尚在巴比倫的猶太余民回歸巴勒斯坦。以斯拉與尼希米重建並治理耶路撒冷,此時全國上下,一致傾心于摩西的律法。諸先知連同瑪拉基逐漸退場,直到新約的施洗約翰。猶太的宗教結果成為表面化,精神已失,所存的只不過是些禮節和形式的外殼而已。亞達薛西王于主前424年駕崩,國中太平四十年。亞達薛西死后,波斯帝國開始逐漸分裂,因為國內已經有了道德和政治的腐敗。
希臘的亞利山大大帝,于主前331年的亞比拉戰役中打敗了波斯的軍旅,于是他的勢力就擴張到希臘本土以外延及小亞細亞,于是希臘時期由此開始。亞利山大大帝是亞裡斯多德的學生,所以他要把希臘的語言和文化傳播在凡他所征服的地區。此舉即歷史中所說的“希臘化(Hellenization)。亞利山大雖治理了希臘,小亞細亞與埃及仍嫌不足,他還野心勃勃,欲征服印度,但他的軍隊拒絕前進。不久以后他因醉酒而死,死時年僅卅三歲。
亞利山大有兩個政策︰征服與合並。亞利山大雖然是個糾糾武夫,能爭善戰,但他如古列一樣,對所有被他征服的國家,都存著一種寬仁大度的精神。他對猶太歷史是有顯著意義的,就是他在兩項偉大的運動上負有相當責任,這兩大運動為未來的福音預備了道路;猶太人的分散,和希臘文化在古代近東人民中的傳播。
亞利山大死后,希臘大帝國為他的五員大將瓜分︰一是西流古(Seleucus)接收了巴比倫;二是帕拉米拉基(Ptolemy
Lagi)分得埃及;三是安提古那(Antigonus)占領了弗呂迦;四是裡西馬古(Lysmachus)承繼了脫瑞斯(Thrace)(古國名,即希臘之西部)與土耳其之東部地方與比推尼;五是卡森得(Cassander)占據了希臘與馬其頓。后三者對于聖經歷史來說並沒有多大的重要性。西流古后來又把敘利亞與腓尼基加入了他的版圖,而帕拉米•拉基把巴勒斯坦合並給埃及。區區的猶大國正夾處于兩大強鄰之間,因此常作二者的戰場。
帕拉米、拉基雖是一員武將,但他也特別關心文化。亞利山大利亞(城名在北非)的最大古圖書館,主要是由他負責與興建的,后來由他的兒子帕拉米•腓拉底弗(Ptolemy
Philadelphus)完成。在此時期內,在亞利山大利亞猶大與希臘的文化有了順利的接觸,由于此項合流的結果,經過好幾個世紀,該兩大文化頗為盛行。帕拉米三世(Ptolemy)是一個戰士,對藝術與文化並不熱心,但正如他的前輩父王一樣,對在埃及與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待遇頗寬。在埃及王朝前三王的治理之下,可以說是猶太人的黃金時代,因為那時正值國中太平,繁榮與進步。
在敘利亞的西流古王朝對于埃及的統治巴勒斯坦生出嫉妒,遂于主前198年經過數次的沖突之后,埃及的帕拉米王朝便失掉了巴勒斯坦而為西流古王朝占領。于是巴勒斯坦受安提歐克大帝(Antiochus
the Great)的統治,在此時期內,構成猶太歷史中最受壓迫的一段時期。西流古王朝卻短命崩潰,因為在西部有強大勢力為鄰,(即羅馬)給它事來了壓力。于特摩派力戰役中,羅馬的軍旅戰勝了敘利亞軍,複于主前190年敘利亞又在麥格尼西亞被打敗了,安提歐克被迫付出一筆龐大的賠款給羅馬,因為走頭無路,為了付出這筆賠款,遂奪取了猶太聖殿的金庫。
主前175年,安提歐克大帝之子克提歐克四世登極為西流古王朝的元首。安提歐克第四自稱為“伊比蕃尼(意即聰慧者),他對此時期迫害猶太人要負完全的責任。他對猶太人所加的虐待,有時出于反複無定,有時是出于奇癖怪行;總而言之,他對待他們是普遍地荒唐殘暴,強迫他們接納希臘的文化與宗教。在安提歐克第四登位以前,猶太人跟他們的統治者頗能和平共處。但如今安提歐克想侵犯他們的思想自由,強迫他們接受希臘的宗教,于是輿論嘩然,群起反抗,起初是出于被動,后來各地的猶太人自動起來叛變。
主前168年,有一位信仰純正又十分敬虔的猶太老祭司,名叫瑪他提亞(Mattathia),為逃避敘利亞王安提歐克的迫害,遂率五子退居于摩顛(Modin)地方。雖在此僅距耶路撒冷五裡的窮鄉僻壤之處,希臘文化推行指導員仍逼迫他執行異邦希臘宗教的禮儀。他予以拒絕,在盛怒之下遂殺死此希臘文化推行員和一個賣國的猶太人,猶太獨立戰爭(或稱瑪克比叛)于是爆發。他們逃離了摩顛,進入山區,召聚義勇的猶太人加入戰爭(此時有哈西典敬虔派加入戰爭),反抗安提歐克並搶劫不忠貞的猶太民區。叛端啟后不久,瑪他提亞死去(主前166年),領導權由其第三子瑪克比猶大(Judas
Maccabee)繼之。所謂“瑪克比叛變”(Maccabaean
revolt)即由此得名。“瑪克比”即“鐵錘者”之意。
在瑪克比領導下的義舉,實為叛變,繼而發展至大規模的全面戰爭,而且戰事順利所向無敵。在以馬忤斯瑪克比擊敗了敘利亞的軍隊,又在希伯侖和耶路撒冷之間東部的山區,連獲勝捷。后卒克服了耶路撒冷,在主前165年聖殿重得潔淨,行奉獻之禮。翌年安提歐克死去,猶太舉國歡騰,普天同慶。安提歐克在陣地的后繼者裡西亞向瑪克比提出具有條件的談和,但遭瑪克比的拒絕,誓言非完全獲得猶太人的自由,戰爭決不能停止。主前160年于亞得撒一次戰役中,瑪克比不幸被殺身亡。
到此時瑪克比運動的歷史,演進頗為複雜,約拿單(瑪他提亞的另外一子)繼承其兄瑪克比猶大抗戰。但由于內部的陰謀與變節,約拿單繼位不果,反遭逮捕。領導權遂落在其弟西門身上。他在主前142年宣布猶太獨立,並以排除敘利亞人在巴勒斯坦的勢力証諸國人。于主前135年西門為其親婿暗殺欲奪其位,為猶太人獲得獨立自由的這個功勞還是歸給西門。
猶太獨立時期是從西門開始,直到羅馬將軍龐培(Pompey)在主前63年進入耶路撒冷為止。西門死時,其三子海卡奴約翰(John
Hyreanus)就大祭司職,掌握軍政大權于己身。為欲求得猶大政治上的獨立,海卡奴遂向羅馬求定盟約,但當時羅馬國在格雷其治下,忙于內政,無暇顧及外交,遂遭拒絕,海卡奴死后,瑪克比王朝開始迅速的衷頹。此時法利賽黨與撒督該黨開始活動,勢力漸大,采取觀望政策,看哪一方面得勝便從中漁利,以求鞏固自己的地位。
海卡奴之子詹尼斯(Jannaeus)因特別恨惡法利賽派,遂征用外國的軍隊殺死六千猶太人。如此猶大複陷于內戰中,六年之內共有五萬猶太人死亡。由于互相攻擊、殘殺、陰謀與黨同伐異,非但陷全國民眾于水深火熱之中,就是王朝家室亦蒙受其害。結果雙方求訴于龐培來調處糾紛。龐培果然來了,大軍進入耶路撒冷以后即殺死一萬二千猶太人。于是瑪克比王朝至此傾廢;瑪克比猶大之火熱精神亦隨之消沉,猶太的獨立運動遂告瓦解,猶大一變而為羅帝國的屬國,為外國的駐軍占領。巴勒斯坦受政治上的捆綁有二千多年。
二、文獻方面
兩約之間的文獻可分為兩大類,即普通所謂之“外傳”(Apocrypha)與“偽經”(Pseudepigrapha)。外傳(隱藏之事)多論及瑪克比叛變並與當時有關的傳奇歷史,其可靠性頗有問題。這些文獻已被古代教會接納,因為它們已被列在希利尼文譯本的舊約聖經中,但為猶太人所拒絕,認為是不正典的,他們把這些文獻看作“外傳”。另一方面,“偽經”向來無人認為有正典性。此類文獻論到世界末日的預言,傳稱為舊約時代這名人(如以諾、摩西、以斯拉)所寫,但其實乃遠在彼等之后所著述的,外傳與偽經之間關系的難題,是由于有些外傳是偽經的,有些偽經是用筆名(非真實姓名)所寫的事實而合成的。所以,明顯可見,這種分類並非是實際的。
主后四世紀,有耶柔米與耶路撒冷的希拉爾(Cyril,827-869,A.C.)用“外傳”來指一切超正典的(非在聖經正典以內的)猶太宗教書籍。有時此名詞有輕視之意,特別是用在“福音外傳”的時候;這是說它們是偽造的,或屬異端的。雖然如此,經年累月,外傳與偽經之間的古舊區分仍沿用下去,但其結果造成許多思想上的混亂。英國學者查理斯(R.H.Charles)就打破以往所通用的慣例,把從前包括在外傳中的瑪克比三書(3
Maccabees)與以斯得拉記下(2 Esdras)列入偽經。近年來有些試圖恢複希拉爾與耶柔米的用法,即指稱所有全體超正典的文獻為外傳。
嚴格說來,外傳包括十三卷,以前曾列入英文聖經中,但后來受到拒絕,認為是非正典的。這十三卷外傳為︰以斯得拉記上(1
Esdras),以斯得拉記下(2 Esdras),多比特書(Tobit),猶得書(Judith),以斯帖附篇,所羅門智慧書,便西拉智訓(Ecclesiasticus),巴錄書(見米三十二12)瑪利米書信,但以理后書,瑪拿西祈禱篇與瑪克比前后書(1
and 2 Maccabees)。
這些聖經外傳是怎樣排入現今聖經中的呢?為尋求這個解答,必須回到聖經古卷之抄寫與翻譯的最初階段。頭一本的拉丁文聖經是在主后二百年從希利尼文譯本翻過來的,那個希利尼文譯本就附帶有外傳。主后391年有耶柔米開始從希伯來與希利尼原文把聖經翻譯成拉丁文。除新約外他指定舊約的二十四卷為正典,其余的他都列入“外傳”。后經友人勸說,他將潦草譯就的多比特書與猶得書列入。主后397年在迦太基大公會議(Council
of Carthage)上決定將外傳加入聖經,認為適宜的讀物,結果外傳被認為和耶柔米的正典平等。
一千多年以后,在天特(Trent)所召開的總會(在主后1546年)席上,天主教為了反應改教者關于聖經正典之限製所提出的問題,遂決定舊約的外傳與被公認的舊約正典有同等的地位。此外,如有任何人對外傳之正典性或對外傳被加入正典的決定有所懷疑者,都應該受咒詛。此決議案又在1870年梵蒂崗會議中加以複決。宗教改革家們反對將外傳加入正典所根據的理由是內証已經顯示出來,外傳是不配與聖經正典並列的。路德馬丁認為外傳是“有用的讀物”所以他把外傳(以斯得拉記上下除外)加入他所翻譯的德文聖經之后。英國聖公會也采取此同一立場,在其三十九條信條中(1562年)說外傳是有益的讀物,但不可以決定有關教義的事。結果,外傳被排除,認為次經。魏克裡夫所譯的聖經將外傳排除,喀弗得爾聖經(Coverdale
Bible)將外傳列入,英文欽定本聖經起先將外傳列入,但在十九世紀以后即將之一律取消。
由于教會對外傳的拒絕,所以一般人士對外傳研究的興趣遞減,但在十九世紀,對福音書背景的關心又加熾烈起來。舊新兩約之間的這一段時期被認為是了解新約事件──即如猶太教內的運動,希臘文化的影響,世界政治的潮流──的契機。因此,人們又對外傳加以注意,認為是此一決定性時期中的考據,在外傳的宗教素質方面來說,又複引起人們的欣賞。雖然現代抗羅宗並沒有將外傳列入聖經正典的企圖,但是對外傳的重視是在爭辯中的,所根據的事實,就是奈西亞前期的教父,都把外傳與聖經正典視為平等。
外傳包括許多文學上的特殊格式︰例如英雄傳記,宗教歷史,宗教哲學,道德格言,有詩意的與有教導性的抒情詩,猶太人的箴言,與所謂啟示錄的奇特風格。關于外傳由來的日期與地點,只能予以概略的說明。外傳的大部分是寫于巴勒斯坦,用希伯來文或亞蘭文寫的,有幾本是用希尼文寫的。約書于主前三百年到主后一百年之間。外傳雖然一致反映了猶太人的心理,但在主后70年以后,當羅馬將軍提多毀滅耶路撒冷的時候,猶太人就不承認這些外傳為正典。結果許多猶太人又重新回到摩西五經,其當然結果就是拒絕一切偽經外傳。不容許任何書籍文獻來與聖經竟爭對抗。此外,又有一個贊助聖經的因素,那就是有一些基督教“派”的著述在民間流傳。據傳迦瑪列第二(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毀后的猶太宗教領袖,為保羅之師迦瑪列之孫)就在主后80年布告,凡讀基督教書籍的猶太人都要受咒詛。為了執行此項決議,曾有一次系統性的毀滅聖經外傳,特別是用希伯來文寫的。這一次猶太人的文化革命運動甚為成功,屬外傳一類的著述幾乎絕跡,但不能阻止基督徒保守這些外傳,也不能阻止猶太人去記憶其中的大部分,這是猶太人所特有的功夫。
《以斯得拉記》(上)是由記述約書亞在耶路撒冷紀念逾越節開始的。本書是由歷代志下,以斯拉記與尼希米記各書所收集的材料寫成的︰其中包括以斯拉記全部(只有幾節省略)。章節的次序不同,因為在以斯得拉記上中把以斯拉記四章七至廿四節排在以斯拉記一章之后,而且又加入不合正典的三個衛士的故事。以斯得拉記下(又稱以斯拉四書)與以斯得拉記上相同的,只是名稱而已,內容完全迥異。這是一部屬于啟示性的書,據稱為以斯拉所發有關世界末日的預言。
《多比特書》乃是一道德故事,多比特系其中主要人物之名。故事的目的是在猶太中反對一切的背道,並高舉主耶和華的律法與宗教。猶得書是一位猶太女英雄的故事,由于她對神的忠勇虔誠,挽救猶太得免沉淪。明顯是一部傳奇小說,目的乃在鼓勵猶太全國人民起來抵抗他們宗教的與國家的仇敵。以斯帖補篇是從以斯帖記正典中所匯集的107節穿抽寫成的。
《所羅門智慧書》雖為外傳中之一,但它確系偽經。該卷是典型的猶太智慧文學,論到罪惡的難題,藉智慧得救之法,神之屬性以及外邦宗教的弱點等問題。《便西拉智訓》是外傳中唯一的匿名(不知著者為誰)書。本書與“所羅門智慧書”一同被列入智慧文學中,其中包括比喻寓言與衛護猶太教的金言錄。《巴錄書》居于啟示性文獻與智慧文學之間,此外又充滿了祈禱與勸勉。
《耶利米書信》是誤稱的,它並不是一封書信,也不是耶利米寫的。這是一封作者不詳,對猶太人所發要保守他們先祖的宗教,並抵抗拜偶像與崇拜異邦宗教之罪的喚起民眾書。《但以理后書》是傳奇故事的匯集,只有一項與正典但以理書有關的記載。《瑪拿西祈禱篇》是靈修文學的最佳作品,其中表明最高尚的悔罪與敬畏的精神。
《瑪克比前后書》雖為兩個不同的著者所寫,但其中所論瑪克比叛變的歷史,對學者是有相當興趣的。前書包括有四十年,即從主前175到135年。本書在文學與歷史性格方面均極高尚。后書所描述的瑪克比事件是從主前176到161年。其中充滿了奇跡的事件或神妙的技能,所以在歷史性方面來說,不如前書比較可靠。
偽經包括︰《埃提阿伯以諾書》,《斯拉文尼以諾書》,《摩西升天記》,《所羅門詩篇》,《巴錄二,三書》,《瑪克比四書》及其他。因為這些書從未被任何宗教團體記入正典,所以並無何重要性,但對于此時期內猶太宗教運動的分辯上,意義頗為重大。
現代聖經學者最為關心的,就是在1947年于死海西北端山穴中所發現的,現在聞名于世的“死海書卷;。這些書卷是在兩千年以前被放在磁器罐裡,置于洞穴中的。這些書卷所以有如此重大的意義其理由有二︰第一,其中包括兩本用希伯來文所寫的以賽亞書抄本,這抄本比從前所有最早的以賽亞書的抄本還要早上幾百年,如此証實了以后的抄本是正確的;第二,其他別的書卷,乃是一從范圍較廣的猶太教中脫出,而欲複興其祖先之古代宗教的隱士社團的文學遺著。此社團如果不真是以斯尼派(Essenes)的分支,那么在生活習慣與所信仰的教義上很象以斯尼派。〔注︰此派系猶太的三大派(法利賽派,撒督該派與以斯尼派)之一。此為一種厭世派,在新約中未曾提及。這不是宗教的一派,不過是一群隱居之士,數目約有四千,守獨身,凡物公用,不蓄奴,親操農務,穿白衣,非常清潔。〕此死海社團(Dead
Sea Community)興衷的日期頗難規定,但由彼等的修道院所占據的期間看來,此一社團乃是在主前140年到主后68年間的一個有組織的團體。
有些學者與新聞記者在死海社團與新約之間,曾注意到某項教義上的相似點,並結論說基督教會乃是從此團體首先所贊助的宗教觀念的延續。但若將死海社團的教訓與新約的教訓作一批判性的分析,就會見出基督的生活與教義的特殊性。死海書卷的永恆意義,乃在于顯明從前這一群無名的猶太人,自猶太教脫出,就暗示了他們反對生活與宗教上的奢侈。
三、製度方面(宗教機構)
在猶太人被擄與基督降世之間,在猶太教中有幾個嶄新的宗教機構得以設立。聖殿為希律所重建,但這不能說是一種新的設施,新的製度。然而會堂、公會與宗教政黨的出現,在猶太教中的確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而且這些機構在新約中又占有意義深遠的地位。
要追溯會堂的發展史,這要回到主前六世紀以色列人被擄的時期。因為被迫離開聖殿所以需要一個地方性的拜神之所與宗教儀式上的規程,于是會堂應運而生。會堂的崇拜不包括獻祭,因為獻祭是惟有在聖殿裡舉行,但只讀摩西的律法(即五經)與先知書。崇拜儀式包括祈禱,唱詩篇,有時講道。在每一會堂中,都有一卷律法書保存在一個小柜子裡。不夠十人,會堂禮拜不能舉行,每個會堂都有它自己的職員,責任分擔。及至猶太人回國時,這種會堂的製度在猶太人的生活中已經根深蒂固,成為地方性的崇拜之所,就是複建的聖殿也不能完全把會堂的地位取而代之,而且這種情形的繼續直到今日。
公會(又稱“山和林”)的淵源不得而知,據傳是在羅馬時代在猶太教中開始的。山和林(Sanhedrin)是由希臘字而來的希伯來譯音,意即“大公會議”(Council)。廣義來說,公會僅指法庭而言,但具體來說,這公會是指著耶路撒冷由七十一人所組成的猶太最高法庭而言。會員多選自貴族、大祭司、長老、文士法利賽人撒督該人,馬太福音第廿六章三節,五十七節以及他處經文,就指明現任的大祭司乃是公會的首席與執行官吏。當羅馬在巴勒斯坦的時期,公會在其勢力上已達登峰造極的地步,因它幾乎完全控製了猶太人的內政,公會有權對有關宗教的,內政的與刑事等法律下判決,在嚴格的宗教的事務上,公會的權柄達于所有分散各地的猶太人。那就是說公會有權審問某項應處死刑的罪犯,從前之福音書中就可以清楚看出,基督的死刑是公會定的。這個最高法庭于主后70年解體,權柄的中心移至北部的提庇利亞。
論到主耶穌當時在猶太教中的黨、派、系,可以說是多得不可勝數,但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文士、法利賽人與撒督該人。以色列王國崩潰后祭司一躍而為全國的主要官吏,文士製度或許是在以斯拉的治理之下設置的。由于重新注重摩西五經(律法),所以對于把律法應用到生活的各方面去特別關心。研究律法並決定其條件與應用的。乃是文士的專責。有時文士被認為猶太律法的專家與護衛者。由此對律法的應用上極端關心,所以就產生出來一個口頭遺傳的團體,后來這個團體的權威就被提高與聖經相等。他們這種努力的實際結果,就是把一連串使人喘不過氣來的宗教禁規硬叫猶太人遵守,因此耶穌猛烈地攻擊此種腐敗的勢力(見馬太廿三章)。文士的遺傳至終將舊約活生生的宗教,一減而為無思想、乏味的、法定的拉比主義。
法利賽派是從信仰純正的猶太人團體中出來的,此說雖未經確定,但有此可能性,這些人被稱為“敬虔派”,他們在安提歐克伊比蕃尼的治下反抗希臘的感化。“法利賽”系希伯來字,意即“分離者”;是在基督教以前的時代反對他們的人所加給的綽號。因為他們是不受希臘的文化所感染的,他們與當日的希臘化的傾向是分道揚鏢的,因而以為是討神喜悅的。法利賽派與文士打成一片,有密切的關聯,他們高舉猶太教崇拜的嚴格方式,而放棄了摩西的律法(Torah)與拉比的遺傳,一變而為普通老百姓的發言人。使他們分離出來而為一法利賽黨的宗教,信仰包括︰死人複活惡人受審判,義人享福樂,相信有天使,神有掌管歷史的主權以及摩西律法的超越性。在法利賽黨中也有教義上的意見分歧,但都屬乎小節。在主耶穌剛出來傳道的時候就受法利賽人的攻擊。他們以為耶穌是破壞猶太律法的。照樣他們也成了耶穌忿怒的對象,因為他們只有屬乎外面之義的觀念。由于他們內在的活力(雖然減退),所以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毀后,他們仍然存在,不過那時的勢力遠不如前了。
初讀福音書的人就會看出來,法利賽派與撒督該派總是互存敵意的,但只有在反對主耶穌的生活與工作上,他們兩派卻能志同道合地群起而攻之。在瑪克比王朝后期兩派互相攻擊的非常厲害,撒督該派在詹尼斯治下頗具勢力,而法利賽派在亞利山太撒羅米(Alexandra
Salome)女王繼詹尼斯之位者的治下很有權威。撒督該一名或許是從撒母耳記下八章十七節所提的大祭司撒督而來。撒督該派的由來也象法利賽派一樣,都是模糊不定,無憑可考;一般學者認為是在瑪克比王朝時出現
。法利賽派對一般民眾發生興趣,而撒督該派卻與貴族和統治階級相往還。他們多關心政治,對宗教的事置之不理;他們的宗教信條與法利賽派的信條相反。有一點頗值注意,他們與基督和使徒們頗有共通之處,那就是他們反對遺傳的權威,而且只承認摩西的律法為宗教上的權威。但他們是反對耶穌的,他們反對耶穌根本上不是因為宗教上的理由,乃是根據他的言論,並他與平民為伍,以致影響巴勒斯坦的政治地位,惟恐樹倒猢猻散,自己的利益跟之瓦解。因為他們與當時的政治機構有如此密切的關聯,所以當這個政治團體在主后70年被提多將軍給消滅的時候,撒督該派也就隨之垮台了。
![]()